文 | 索马里
「那不勒斯四部曲」中文版责任编辑
没有读过「那不勒斯四部曲」小说的读者在进入 HBO 的改编剧集之前, 不妨将费兰特引用过的那句谚语在心中牢记——「 和敌人在一起的时候,我看顾我自己。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,上帝看顾我。」

埃琳娜·费兰特「那不勒斯四部曲」
《我的天才女友》《新名字的故事》
《离开的,留下的》《失踪的孩子》
这样你便不会在看似日常的剧情中忽略了这部剧集的要点。这句谚语可以粗暴地概括费兰特的四部曲,及 HBO 改编的第一部《我的天才女友》。它在提醒我们去正视友谊的复杂性(尤其是女性友谊)。友谊远非奖惩分明或者界限清晰的比赛,也不是血肉模糊的丛林法则,更不是情感和权力的乌托邦。

《我的天才女友》

和敌人相处的时候,我会警惕自己面临的危险的阈值。但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,只有上帝知道我朋友脑子里的想法。我在友谊里的命运如何只有我的上帝、我的朋友才能掌握,我是多么被动、无辜而「纯洁」。
不管你有没有看过书,HBO 版的观众对主角莱农的第一印象可能就是她的这种「无辜」。第一季《我的天才女友》改编严格来说几乎完全遵循原书。从莱农和莉拉充满暴力的童年开始,终止于两个好朋友命运彻底分化的16岁。一切起源于莱农对莉拉在课堂上展现出来的耀眼智力的嫉妒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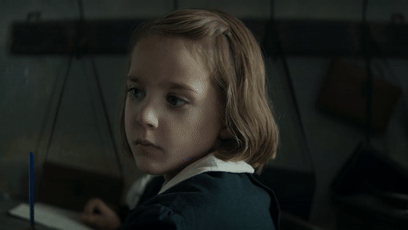
当莉拉将莱农的布娃娃扔下街区恶霸堂·阿奇勒家的地窖时,她的反应模式是——此后也一再是——「你怎么做,我就怎么做」。她跟随莉拉去找人人恐怖的魔鬼要回自己的布娃娃,莉拉在楼梯上拉住她的手,「这个举动彻底改变了我们之间的关系」。
莉拉是莱农的榜样、模仿对象、镜子,也是她一生的主题(subject)或唯一真正热爱过的「客体」。所以,片中的诸多镜头更接近于莱农对莉拉的凝视(而不是相反)。莱农学习莉拉的学习方法,她应对恐怖的方式。

当莉拉的命运因为家人不支持她继续上学而早早遭受摧毁时,莱农可能也是街区里最为悲伤的人。莉拉辍学后在家里的鞋铺打工,最后选择早早结婚,留在那个人人活得卑微如乞丐的社区,试图凭借自己的才智改变一切。
与此对应的是,莱农在莉拉的鼓励和提醒下,选择了用教育改变自己。尽管她最大的、无法说出口的恐惧就是,如果她的好朋友有机会和她一起上学,一定会表现的比自己优异很多。

「你很擅长招人喜爱, 这就是我们俩从小的差别。人们都很害怕我,却不害怕你。」 莉拉结婚前对莱农这么说,其中的意味只有读者心底明白。
显然,电视剧的旁白也好,对白也好,在大部分时候都无法具备文字传达「整体真实」的能力。观众不具备小说编织的厚实的心理纹路,对人物的行动和对话的领会往往也会陷入无辜的附会。毕竟什么样的镜头能传达,「彻底改变了我们之间的关系」在莱农的心里具有的可怕的象征意味呢?
但意大利导演萨维里奥·科斯坦佐(Saverio Costanzo,其导演作品包括《饥饿的心》《质数的孤独》)凭着其简洁和准确的改编,通过高度浓缩的剧情、完美的摄影和场景设定中,不断强化的,就是友谊的那种复杂对立,在这点上,他试图合格地传达这种对立,如同战争的友谊和成长。

萨维里奥·科斯坦佐
导演对作者和原著的敬畏被所有的媒体都注意到了,以至于,对他最剧烈的批评无非也是「还原原著的苦心付诸东流」。不过抛开原著,科斯坦佐所遥远致敬的意大利「新现实主义」电影风格,在第一季8集中已经有明确的呈现。
「工人阶级的普拉达广告,笼罩在谦卑的柔情之下」——《纽约客》的一篇文章如是概括前八集的主题,也算得体。
这篇文章注意到剧集已经超越了女性友谊的刻画,其精湛的制作水准其实是谦卑地服务于一部沧桑的「阶层跨越史」。和新现实主义的很多代表作一样,这样的阶层跨越,十有八九,最后都陷于失败、沉默。

确实,第一季里,导演花费大量笔墨的,除了那段并非势均力敌的友谊之外,更多的就是阶层的对立,而有因为故事的主轴落在脆弱的童年、缺乏弹性的青春期,其中剧烈碰撞的暴力和失落愈发动人。
第一季里,放高利贷的家庭掌握着街区命脉,他们的子女可以在学校里被老师额外照顾,他们可以最早享受物质的愉悦,和精神上对他人的奴役和践踏;而底层的儿童(后来的少年)们,他们脸上遍布贫穷的影子,无论是街区卖水果的恩佐,当技工的安东尼奥或者身为共产党的父亲被关进监狱、只能去当泥瓦匠的帕斯卡莱,包括莉拉,他们在第一部里,其实都无法有效地阶层跨越,除了莱农。

还有莉拉和莱农居住的那个透着「贫穷的光」的那不勒斯社区,剧组也花了一百多天在那不勒斯郊外的一处地方复制出来。它给人的感觉如此荒凉。尘土飞扬的大路,和每天粗鲁经过的火车都预示着这是一个没有希望、所有人都渴望逃离的地方。
尤其是对非专业演员大量的起用——书里几乎所有的演员都是来自海选(一共9000人次),他们在荧幕上有一种专业演员难有的亲和力。
扮演童年莉拉的Ludovica Nasti,黑瘦,有近乎倔强的生命力,和街区里所有向生活屈服的人形成鲜明的对比。

科斯坦佐说「她可能比我们所有人对生命的领悟都要多」——很少有观众知道,4岁时Ludovica被查出患有白血病,此后经历了一系列化疗。为了拍摄这部剧,她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同意剪掉了自己的头发。
但Ludovica的眼神热烈得灼人,她很好地体现了智力在童年时代所具有的两面性,那既是启发性的,可以带领朋友一起憧憬未来,让对方一步步摆脱对父母、逃学和权威的恐惧;也可以是摧毁性的——莉拉的家人对她的控诉,尤其是她哥哥里诺挂在嘴上那句,无外乎都是「你想毁掉一切吗,婊子?」

言归正传,康斯坦佐的剧集,并没有像维斯康蒂的镜头,将流逝变成「不加批判的怀旧」,康斯坦佐严格来说构成了维斯康蒂的对立面,他充满批判地看待流逝,他借用语言、惩罚、暴力等等,解构了家庭、街区和学校的权力结构,让我们看到,所有的个体如何被自己身处的环境一步步勒令屈服,但并非完全消极地同时展现了人身上那种和这种环境、和自己的内在局限或和解或斗争的过程。
从这个角度来说,他解构了童年、青春,将其本质化为费兰特真正的主题——成为(become),生成(becoming),在最理想的情况之下(如果摄影机有不受限的时间,可以将小说逐页改编影视化),我们就更能看到这部史诗(及其影像版本)的普适性所在。

囿于目前影视剧改编不可避免的省略或强化,我们通过画面进入这个故事的过程,和用文字抵达的过程可以说注定是一种礼貌的雷同。套用那句谚语,在小说里,「莱农」会看顾我们;而在电视剧里,摄影机会看顾我们。我们必须将自己在叙事上对于莱农百分百的依赖让位于摄影机,它并不是完全以莱农的「becoming」为线索的。
摄影机为我们带来了原著里缺乏的对暴力具体的、肉体化的呈现,摄影机可以展示一个男人(帕斯卡莱的父亲)如何被高利贷团伙摔到高墙上,街区所有人,包括童年的莱农和莉拉都是软弱的目击者;摄影机也可以展现权力的高下在现实生活里到底是什么样子。

比如最后一集,斯特凡诺去莉拉家的鞋铺里试鞋,莉拉下去给斯特凡诺穿鞋, 蹲在地上,摄像机从她未婚夫的肩膀向下俯瞰,和莉拉抬起的脸正面相对的,其中性和权力的意味不能更明显清晰——而这种他者的视角在小说里是缺位的。
也因为我通过小说建立的对莱农的「亲密」,所以在某些时候会对摄影机的这种省略有些无奈,如果算不上愤怒的话。印象最深的是青春期的章节里,莱农已经深陷在对尼诺的精神迷恋和对安东尼奥现实恋爱的矛盾中。

她在课堂上和宗教老师顶嘴,因为老师大肆攻击共产党(帕斯卡莱的父亲曾经是个正直的共产党),她不相信老师说的那套,说人们信教「就相当于整个城市被地狱之火燃烧时,我们还在收集和崇拜画像」。
她被老师驱逐到走廊上,撞见尼诺,尼诺鼓励她写一篇分析南部贫穷现状的文章。这对于当时的莱农几乎是一道充满命运启示的亮光。
我想着自己的 小文章发表在杂志上的情景,内心充满着期待,夹杂着甜美和不 安。在内心深处,我觉得自己的名字——埃莱娜·格雷科印到杂 志上时,自己才算真正活过,我对别的事都漫不经心,一直期待 着文章出版的那一天。
她激动地写了文章,并成功地让莉拉帮她修改文章。在电视剧里,莱农对尼诺离去的背影投去的只有仰慕的目光,之后她的男朋友安东尼奥来接她的时候,她频繁回头,只是顾忌尼诺看到自己和男朋友在一起。
但电视剧在这里将女性在爱情中其中从未缺席的「自我关注」彻底删减掉了。视觉语言给观众的结论是,莱农全身心地只是想得到尼诺的肯定,她退化成一个渴望等待肯定的形象,而无法传递出小说里莱农对尼诺又爱慕又轻视的荒谬:
他甚至没有告诉我,杂志什么时候 出来,怎样才能获得那份杂志,我也没有勇气问他。他的态度让我很厌恶,加上他离开时,我从他远去的身影中看到他父亲走路的样子。
……
我让安东尼奥来学校接我,他马上就按照我的要求来了,一 方面他很迷惑,另一方面又很感激我能让他来。最让他惊讶的是:我当着所有人的面拉住了他的手,和他十指交缠。我一直拒 绝那样和他走在一起,无论是在城区里面还是在外面……那次,我就是这么做的,我知道尼诺看到了我们。我想让他知道我是谁:我的文章比他写得好,我会在他发表文章的地方发表自己的文章,我在学校学习很好,比他还好,我还有一个男人,这就是我的男人,因此我不会像一只忠诚的小狗一样,跟在他屁股后面。
仅仅是书中普通的一段心理叙述,但可以说明对故事改编构成的挑战几乎是总体性的。我猜,导演放弃必要的情节的忠诚,放弃加入莱农让男友来接自己,她如何对骄傲的莱诺又钟爱又厌恶,是因为莱农的这段心理活动只有她自己知道,无法和画面里其他人沟通。
但导演也选择用其他的方式,将莱农的秘密补偿给我们。比如莱农陪莉拉去试婚纱的时候,雄辩地说服了莉拉的婆婆和小姑子,让她们放弃让莉拉穿一条非常浮夸迂腐的婚纱。
莉拉嫉妒地说,「你从哪儿学到这些的。用这样的话去嘲弄别人。」莱农镇定地位自己辩护,说自己并没有夸张,也没有像冒犯,我在学校里学习的就是这些——她这么说是明显激起莉拉的嫉妒,因为后者没有在学校学习的机会,她无法学习如何用考究的语言去控制别人的想法。
看到这一段时,我几乎误认为这是对小说的严格复述(实际相反,这是编剧的杜撰对话)。但也可以说明,摄影机「看顾」我们的时候,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摆脱了莱农的视角产生的专断,我们从小说幽闭性的叙述中可能无意识地逃离出来,这对读者而言未尝不是一种有趣的祛魅。但导演始终带着的「谦卑的柔情」,让我们在遭遇(影像对文本的)轻微的背叛时,也并没有太多愤慨。



